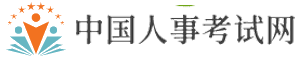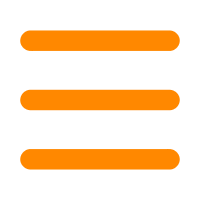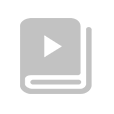刑事羁押作为刑事诉讼过程中所采取的强制手段,是为了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据法定的实体条件和程序需要,由负责刑事侦查的机关采取的暂时剥夺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性方法。[1]国内的刑事羁押包含刑事拘留和逮捕这两种手段,是刑事诉讼中的五种强制手段中最为严厉的方法。因为刑事羁押所具备的剥夺人身自由之严厉性,因此,其不能滥用问题备受强调人权保护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及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关注;在中国,怎么样有效控制刑事羁押以降低、预防滥用的问题,在近几年来的刑事司法规范和程序的改革讨论中,也是个热门问题。在对刑事羁押的各种控制办法中,就刑事诉讼规范和司法程序的层面而言,司法控制是其中最为要紧的一种方法。本文将基于对中国目前的刑事羁押规范的特征、国际人权公约的有关需要与人权保障的需要所作的剖析,研究刑事羁押的司法控制问题,以期能够帮助国内的受刑事羁押之人就其刑事羁押是不是合法可以诉诸司法的机制早日打造。
1、 国内的刑事羁押规范的一个显著特征
国内的刑事羁押规范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缺少由联合国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中之刑事司法标准所需要的“人身保护令”规范。[2]在国内的刑事羁押规范中,两种暂时剥夺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强制手段,即逮捕、拘留,除去法院直接决定的逮捕,在某种程度上符合人身保护令规范的某种需要,检察院批准或决定的逮捕和拘留、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决定的拘留,均与人身保护令的需要不同。这里所说的不同,主要有两层含义:
(一)缺少司法控制
中国的刑事羁押缺少司法控制,一方面,这是指刑事羁押事前未经司法审察;其次,也是愈加要紧的问题在于,在刑事羁押之后,司法机关不可以对刑事羁押的合法性进行审察。然而,依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9条第4款的规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有资格向法庭提起诉讼”,以便由法庭裁决逮捕或拘禁是不是合法。
中国的刑事羁押事前未经司法审察,主如果指刑事拘留这种可达数天甚至于数十天的较长期羁押,仅由负责侦查的机关决定,事前不需要经过司法机关的审察、批准。至于逮捕,事前虽说应经过法院决定或检察机关的批准,但这种法院决定或检察机关的批准是不是是司法控制,尚是个疑问。对此,后文马上予以剖析。
在我看来,中国的刑事羁押缺少司法控制,愈加要紧的问题在于刑事羁押之后司法机关不可以对刑事羁押的合法性进行审察,主要基于国内的逮捕与羁押合一这个特征。在刑事诉讼法制发达国家,实行逮捕与羁押离别规范,逮捕只不过捕获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到案的强制手段,至于捕后是不是予以刑事羁押,则由司法机关审察后决定。在这种体制中,对羁押的司法控制与国内的状况并不相同。国内的逮捕与羁押合一的特征,使得对刑事羁押的事后审察的重要程度变得愈加突出。显然,在这种体制中,逮捕之后对其进行相应的司法控制,愈加有益于达成通过司法控制所欲达到的两个目的,即审察刑事羁押的合法性、降低刑事羁押手段的广泛使用。就此而言,对刑事羁押事前所进行的司法审察,用途有限。由于,对刑事羁押的合法性和必要性的认识,逮捕之后的审察是事前审察所不可替代的,毕竟,事前审察所依据的材料因单方面源于侦查机关而具备很大的片面性,使审察的公正性不可防止地遭到影响。因此,在刑事羁押缺少司法控制这个特征中,对中国而言,更应引起注意的是其中的缺少逮捕之后的司法审察,而不是逮捕之前的司法审察。另应该注意的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9条第3款规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飞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该规定对于中国逮捕之后的司法审察问题之解决,更显出其独特的意义。
(二)刑事羁押期限较长
中国刑事羁押的期限不只较长,而且因决定刑事羁押的机关及诉讼阶段和诉讼中的具体问题的不同而有差异,比较复杂。比如,公安机关的拘留期限分为一般期限和特殊期限这两种。一般期限是指在符合刑事诉讼规定的拘留条件时,对犯罪嫌疑人的拘留期限。这一期限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对被拘留人的讯问时间。依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被拘留人应在拘留后24小时之内进行讯问。假如经讯问,发现不应拘留的,应即予以释放;发现需要逮捕而又不符合相应条件的,则应改变强制手段,或者取保候审,或者监视居住。另一部分则是提请检察院批准逮捕的时间。这一期限,是在拘留后3日内,在特殊状况下,提请批捕的时间可以延长1至4日,而检察院则在接到批捕提请后7日内作出是不是批捕的决定。特殊期限是指在法律规定的特殊状况下拘留后提请批捕的时间可以延长30日。这类状况包含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等,对其中的重大嫌疑分子,可以对拘留后提请批捕的时间延长30日。而检察院机关在自侦案件中,假如决定拘留,不只在适用的条件上不同于公安机关的拘留,而且在期限上也不同于公安机关的拘留,即对被拘留的人,在24小时之内进行讯问,觉得需要逮捕的,应在十日内作出决定;在特殊状况下,决定逮捕的时间可以延长1至4日。至于逮捕的期限,在法院审判之前的侦查阶段和审察起诉阶段,并不一模一样;而且,因侦查机关分为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两家,在侦查阶段也不一模一样。在公安机关负责侦查的案件中,逮捕的期限也分为一般和特殊两种状况。通常情况,是指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刑诉法规定为两个月;案情复杂、期限届满而侦查在此期限内不可以终结的,可以报请上一级检察院批准延长一个月。而检察院审察起诉阶段的逮捕期限,因为受审察起诉期限的限制,相对于侦查阶段的逮捕期限,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即普通案件,期限为一个月;重大、复杂的案件可以延长半个月。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在审察起诉时,对于需要补充侦查的,可以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也可以自行侦查,而补充侦查的期限为一个月,且可以有两次补充侦查,因此,审察起诉阶段的逮捕期限,因为补充侦查的存在,事实上可以再延长两个月
因为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刑事羁押期限较长,[3]因此,与联合国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所规定刑事羁押应得到司法部门飞速而有效地控制的规定,明显不相符合。比如,《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9条第3款规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被逮捕或拘禁的人,应被飞速带见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并有权在适当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该条第4款则规定:“法庭应不拖延地决定拘禁他是不是合法与假如拘禁不合法时命令予以释放”。[4]
当然,国内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没对刑事羁押规定“人身保护令”如此的控制手段,但也并不是没相应的制约机制。比如,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对刑事羁押就好使着肯定的控制职权。因此,对大家来讲,需要讨论的问题并非刑事羁押是不是有相应的控制,而是是不是应当规定“人身保护令”如此的司法控制手段,即是不是应通过司法的渠道对刑事羁押手段予以有效控制。
2、 司法控制刑事羁押的必要性
我以为,讨论通过司法的渠道对刑事羁押手段予以有效控制的必要性问题,第一需要确定通过“司法渠道对刑事羁押手段予以有效控制”的意思。就此而言,确实存在着很多应予澄清的问题。比如,检察院通过批准逮捕等方法对刑事羁押手段所施加的控制,是不是是“司法渠道对刑事羁押手段予以有效控制”,就是个需要探讨的问题。虽然宪法等有关法律规定了国内的检察院与法院相同,都是司法机关,并且,作为法律监督机关,依据刑事诉讼法及有关法律的规定,检察院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极为要紧,履行对公安机关批准逮捕的申请进行审察的职责。然而,国内检察机关通过批准逮捕等方法对刑事羁押手段所进行的控制,与联合国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所规定的“人身保护令”,并不相同。依据《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所规定的人身保护令的需要,审察刑事羁押合法性的应是审判官或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在这里,“其他经法律授权行使司法权力的官员”的意思虽有不确定性,国内的检察院好像也可以包含在内,但大家对此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字面含义。显然,要紧的并非控制刑事羁押的人与机构之名字是不是有“司法”的字号,而是该控制刑事羁押的人与机构在审察刑事羁押合法性的时候,是不是适用了司法程序;是不是因此可以向被刑事羁押之人提供与剥夺自由问题相适应的程序保证。
对此问题的理解,大家可以借鉴欧洲人权法院的讲解。欧洲人权法院在1971年的“流浪汉案件”中讲解了被拘禁人可以求助的“法院”的性质:“为了构成如此的法院,当局需要提供在剥夺自由事情上适用的基本程序保证。……所遵守的程序具备司法的性质,可以向有关的个人提供与剥夺自由问题相适应的保证……”欧洲人权法院觉得,《欧洲人权公约》第5条第4款(关于审察拘禁合法性的机构)的意思,在于该机构需要具备(独立于行政部门和党派)司法性质。[5]
因为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承担着指控犯罪的责任,与负责侦查的公安部门在刑事诉讼中的职能有着某种程度上的一致性,因此,其在决定或审察刑事羁押合法性的时候,是不是确实具备“独立于行政部门的司法性质”,就是个疑问;况且,更要紧的是,国内的检察机关在决定或审察刑事羁押合法性的时候,所适用的程序并不具备司法的性质,不可以提供在剥夺自由事情上适用的具备司法性质的基本程序保证,因此,为了使刑事羁押得到司法的有效控制,国内有必要打造由法院审察刑事羁押合法性的机制。
第二,需要进一步认识司法控制刑事羁押的意义。“人身保护令”,即由法院审察刑事羁押合法性的机制,其主要意义有两个,一是程序意义,即为被拘禁者提供可以申诉的机会,以通过公正司法的渠道来审察对其的刑事羁押是不是合法;二是实体意义,即通过司法审察以切实降低刑事羁押,有益于达成《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9条第3项所规定的“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在我看来,由法院审察刑事羁押合法性的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虽说是相互关联的,但,两者具备互相不可替代的意义。
就其相互关联的意义来讲,法院审察刑事羁押合法性的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都是基于无罪推定原则的。正是基于无罪推定原则的需要,“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在现代的刑事诉讼法律规范中才需要并应当予以确定。显然,刑事羁押所具备的临时监禁特征,作为一种(在剥夺人身自由方面)与刑罚相当的手段,依据无罪推定原则的需要,若非必要及有相应的证据证明这种必要性,通常来讲不应使用,而应予以保释。因此,依据无罪推定原则的需要,假如刑事羁押不合法或并不是需要的手段,则应依据法律的规定予以保释,以降低刑事羁押。其次,由法院审察裁断刑事羁押的合法性问题,审察刑事羁押是不是是需要的手段,也是与无罪推定原则相联系的。由在刑事诉讼中相对于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而言处于中立地位的法院,通过公正的司法程序审察刑事羁押的合法性、必要性及决定对被非法拘禁者予以释放、降低刑事羁押,正是无罪推定原则基本精神的反映,由于无罪推定原则的精髓在于:通过公正的司法程序以保障被刑事追诉之人的合法权益。
然而,由法院审察刑事羁押合法性的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虽说是相互关联的,但,两者具备互相不可替代的意义。一方面,由法院审察刑事羁押合法性、必要性,虽然使审察刑事羁押合法性的程序意义得到达成,但这并不势必意味着实体意义的达成。实体意义上的成效,如非法刑事羁押的排除及非必须的刑事羁押之降低乃至消除,以达成“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的问题,并不可以因此而可以简单地获得解决。因此,大家不可以只不过满足于由法院审察刑事羁押规范的打造。其次,非法刑事羁押的排除及非必须的刑事羁押之降低,虽然也存在通过其他渠道达成的可能,但“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即便成为现实,也并不意味着法院审察刑事羁押的程序意义的达成。[6]显然,由独立而公正的司法机关通过司法程序才能显示的程序公正,是其他机关通过其他方法所很难达到的。就此而言,法院审察刑事羁押合法性的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都是大家需要予以充分考虑的问题。
[1][2]下一页